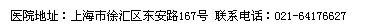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聋症 > 聋症症状 > 王淑芝向唯一的听众学习激励之道
王淑芝向唯一的听众学习激励之道
向“唯一的听众”学习激励之道
山东省邹平县黄山实验小学王淑芝
郑振铎的《唯一的听众》是篇极好的文章。场景如画,语言如诗。
文中的“我”,可以让学习者认识到,只要不放弃,努力一定会有成果。文中的老人,我们可以让人们感受“善良”与“智慧”。
但我觉得,作为教师,读过这篇文章后,最应该做的是从她,这位“唯一的听众”,这位满头银发的教育者身上,学习激励之道。
是的,激励之道。
“我”从一个“音乐方面的白痴”,锤炼成一位可以在“成百上千的观众”面前从容演奏并令观众痴迷的小提琴手,老教授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但我们通读全篇,发现老人并没有给“我”进行过哪怕一点点的演奏技巧方面的指导,她所做的,是用一种令我们叹服的激励之法,激发出了“我”自身潜能(不教之教)!这样成功的教育之道,我们怎可不细细揣摩呢?
在笔者看来,老人的激励效果良好的第一个关键是:她的激励是适度的。
设想一下,如果老人直接说:“你拉得好极了。”会有后来的成果吗?可以说肯定不会。“我”当时拉得确实不强,自己认为是把“锯床腿”用的锯子带到了树林,当时正处在懊恼与自我诅咒的情绪中。如果有人说你拉得好极了,一定会被认为是嘲弄。也许老人是发现了在“锯木头”的声音中有些奥妙,但难以言传,老人做的是多么巧妙啊,她说:“我猜想你拉的一定非常好,只可惜我的耳朵聋了。”这样就让“我”因为自己拉的不好所产生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卸掉了。这启发我们,我们的激励一定要准确而适度,不要随便夸大——错了也说什么你真棒。我们不要以为孩子不懂,他们会敏感地感觉到你是真心的夸奖,还是程序地应付。
老人的激励还是变化着的。在“我”的水平逐步提高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老人的激励也在发生着变化,在逐步加深着,这我们可以从文中清晰地读到。这需要我们对学生成长阶段的洞察与学生发展阶段做准确了解,才能进一步做到适度。
还有一点我们不能不注意到:老人的激励是持续的,而不是一时的。
老人之所以成功,这一点很重要。她说要做人家的听众,“就在每天早晨”,那是说到做到,在“我”“每天清晨”到树林中练琴的时候,总可以看到这位“唯一的听众”,这位先是被认为耳聋,后被告知是“首席小提琴手”的老人。想想有些人说的一次笑容、一次家访、一次表扬就让孩子改天换地脱胎换骨的教育神话,我们更应该看看这篇《唯一的听众》。为师者的激励与教育,应该是持续的。这需要耐心,不要企图找到什么一把什么钥匙,“吧嗒”一声,把一把锁头开开了,我们就可以一劳永逸。没有的,那是一种将教育简单化的梦幻,我们不要受此迷惑。试想,老人只说那一次,以后不来了,“我”会那样坚持下去吗?
然而笔者认为老人的激励之所以能出现那样的效果,最关键的还是这样一点:她做的是顺势的行为,而不是强力的牵引。
文中的“我”,虽然被称为“白痴”,但其本人对小提琴的兴趣是那样难以割舍。他被家人嘲笑,“不敢在家里练琴”,他就早起到树林中去练习。这样的执着是一般人难以企及的。在他因为没有进步而沮丧懊恼时,老人给予了他激励,让他坚持了下去,但这份激励,是在“我”兴趣的方向上的助推,是一种顺势的行为。
这给我们的启发是,我们应该努力去了解我们教育下的儿童,去了解他们的天性,顺其天性做他们生命成长的助力,而不能为了完成我们的工作任务,凭我们的意愿和标准,去“塑造”孩子,让孩子变成我们希望的样子。那样往往劳而无功甚至适得其反。不是有这样一句话吗?我们总想把我们的孩子培养成狮子,但结果除了狮子之外的那些学生都没有变成狮子,反而变得什么都不是了。
我们要做老人这样的“顺势”的激励,作为教师一定要提高自己的眼光。我想,老教授之所帮助“我”一定是经过选择的。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在艺术上的成功,都不是仅凭努力就可以做到的,这个“白痴”身上,一定有着某种“爸爸妹妹”们无法觉察而老教授凭借自己敏锐的感觉捕捉到的某种素质,所以,老教授才开口,让“我”坚持下去。我们也应该成为老教授那样具有敏锐感觉的教师,去发现我们的孩子身上的优势发展区域,如此,我们的激励才会成为顺势的、有结果的激励。
还有最后一点,文中的“我”没有辜负老人的期望,老人一定也非常宽慰。但“我”再成功,再辉煌,哪怕心里再感念这位“唯一的听众”,都没有办法在老人的考核表上加上一厘半分,老人施以援手的目的是让一个音乐生命开花结果,让世界多一个音乐的灵魂,而不是她自己的教育成绩。这是一种境界,是我们应该努力达到的层次。
现实中,许多教育者经常发出“寒心、失望”的声音,觉得自己付出了那么多,学生却就是如顽石般不肯改变。让我们多读两遍《唯一的听众》吧。学学老人激励之道,学学她的不教之教。
附:《唯一的听众》原文
唯一的听众落雪
用父亲和妹妹的话来说,我在音乐方面简直是一个白痴。这是他们在经受了我数次“折磨”之后下的结论。我拉出的小夜曲,在他们听起来,就像是锯桌腿的声音。我感到沮丧和灰心,不敢在家里练琴。我终于发现了一个绝妙的去处,楼区后面的小山上,有一片年轻的林子,地上铺满了落叶。一天早晨,我蹑手蹑脚地走出家门,心里充满了神圣感,仿佛要去干一件非常伟大的事情。林子里静极了。沙沙的脚步声,听起来像一曲悠悠的小令。我在一棵树下站好,庄重地架起小提琴,像一个隆重的仪式,拉响了第一支曲子。尽管这里没有父亲与妹妹的评论,但我感到懊恼,因为我显然将那把锯子带到了林子里。我不由得诅咒自己:“我真是个白痴!”当我感觉到身后有人而转过身时,吓了一跳,一位极瘦极瘦的老妇人静静地坐在一张木椅上,双眼平静地望着我。我的脸顿时烧起来,心想这么难听的声音一定破坏了这林中和谐的美,一定破坏了这位老人正独享的幽静。我抱歉地冲老人笑了笑,准备溜走。老人叫住我,说:“是我打搅了你吗?小伙子。不过,我每天早晨都在这里坐一会儿。”有一束阳光透过叶缝照在她的满头银丝上,“我猜想你一定拉得非常好,只可惜我的耳朵聋了。如果不介意我在场的话,请继续吧。”我指了指琴,摇了摇头,意思是说我拉不好。“也许我会用心去感受这音乐,我能做你的听众吗?就在每天早晨。”我被这位老人诗一般的语言打动了;我羞愧起来,同时暗暗有了几分信心。嘿,毕竟有人夸我了,尽管她是一个可怜的聋子。我于是继续拉了起来。以后,每天清晨,我都到小树林去练琴,面对我惟一的听众——一位耳聋的老人。她一直很平静地望着我。我停下来时,她总不忘说一句:“真不错。我的心已经感受到了。谢谢你,小伙子。”我心里洋溢着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很快,我就发觉我变了,家里人也流露出一种难以置信的表情。我又在家里练琴了,从我紧闭门窗的房间里,常常传出基本练习曲。若在以前,妹妹总会敲敲门,装出一副可怜的样子,说:“求求你,饶了我吧!”而现在,我已经不在乎了。当我感觉到这一点时,一种力量在我身上潜滋暗长。我不再坐在木椅子上,而是站着练习。我站得很直,两臂累得又酸又痛,汗水早就湿透了衬衣。同时每天清晨,我还要面对一位耳聋的老人尽心尽力地演奏;而我惟一的听众也一定早早地坐在木椅上等我了。有一次,她竟说我的琴声能给她带来快乐和幸福。我也常常忘记了她是个可怜的聋子。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终于有一天,我拉的一曲《月光奏鸣曲》让专修音乐的妹妹感到大吃一惊。妹妹逼问我得到了哪位名师的指点,我告诉她:“是一位老太太,就住在12号楼,非常瘦,满头白发,不过——她是一个聋子。”“聋子!”妹妹先是一愣,随即惊叫起来,仿佛我在讲述天方夜谭,“聋子?多么荒唐!她是音乐学院最有声望的教授,曾经是乐团的首席小提琴手!你竟说她是聋子!”我一直珍藏着这个秘密,珍藏着一位老人美好的心灵。每天清晨,我总是早早地来到林子里,面对着这位老人,这位耳“聋”的音乐家——我唯一的听众,轻轻调好弦,然后静静地拉起一支优美的曲子。我渐渐感觉我奏出了真正的音乐,那些美妙的音符从琴弦上缓缓流淌着,充满了整个林子,充满了整个心灵。我们没有交谈过什么,只是在一个个美丽的清晨,一个人默默地拉,一个人静静地听。老人靠在木椅上,微笑着,手指悄悄打着节奏。她慈祥的眼睛平静地望着我,像深深的潭水……后来,拉小提琴成了我无法割舍的爱好,我能熟练地拉出许多曲子。在各种文艺晚会上,我有机会面对成百上千的观众演奏小提琴曲。但总是不由得想起那位耳“聋”的老人,每天清晨里我唯一的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