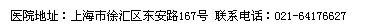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聋症 > 聋症护理 > 文学小说袁正华岁月有痕
文学小说袁正华岁月有痕
作者简介:袁正华,58岁。四川平武古城中学教师,平武作家协会会员,四川老年诗会成员,有作品见《绵阳晚报》《中国诗文网》《山泉杂志》等。
岁月有痕
袁正华
一九七七年二月的最后一天,是学校春季开学的前一天,刚好吃过午饭,贫管会副主任突然来到我家。贫管会,全称“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归大队党支部领导,主任的位置非大队党支部书记莫属,成员全是清一色的贫农,都是劳苦大众出生。
贫管会副主任姓赵,弓腰驼背,满脸的麻子。他双眼一条线,上齿比下齿略显突出,说不说话,都吊着口水。一年四季都披着政府发的草绿色衣服,戴着草绿色帽子,穿着布鞋。布鞋是他老婆熬更守夜亲手做的。自打新鞋上脚,鞋后跟就没有人见他蹬起过。为了这事,有与他成分一样,年龄差不多,都是贫农,不怕他的人,当众戏说他:“赵主任呢,以后做鞋,干脆让你婆娘就不要给你做鞋后跟。一来,节约布料,省钱。二来,少耗费些你婆娘的时间和精力,省着晚上自己好多用。”他每次总是皮笑肉不笑地回答:“龟儿子杂种些,少给老子说骚话,当心老子抓住你娃娃些的辫子,弄死你狗日的一个个的。”
赵副主任,人还没有到,声音早就到了,来到我家大门前,左脚抬起,踩着大门门槛,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母亲见状,连忙端起一根板凳,一边招呼,一边用衣袖抹去凳面上的灰,安放平稳后,请赵副主任坐。
父亲从衣兜里掏出吃叶子烟的那套行头,解开装烟末的布袋,细心的装满叶子烟,还特意把烟叶中的烟骨头挑了又挑,选了再选,生怕赵副主任吸烟时接不上火。一切准备妥当,父亲当着赵副主任的面,将烟杆入口的一端用手反复擦了好几遍,然后弯下腰,双手将烟杆递给赵副主任,轻声说:“来,整一袋。”
赵副主任抬起头,歪着脑袋,斜眼看了看父亲,有点俏皮,有些得意地说:“还是你整。”
说话间,赵副主任不紧不慢地用右手解开上衣口袋,左手拇指和食指巧妙配合,将装烟的上衣口袋撑得开开的,右手伸了进去,从里面拿出一包“春燕牌”香烟,连烟带盒又转到左手,然后,右手掀开盒盖,抽出一只,很潇洒地将纸烟的一端在烟盒上上下抖着,连看都不看父亲一眼,说:“我现在抽这个了。”
父亲红着脸,缩回了递烟杆的手,回到一边,坐在底朝天的背篼上,握着烟杆,埋着头。
赵副主任一支烟抽了大半,故意咳了两声嗽,开始发话:“老李,是这个样子的,我今天是代表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来宣布昨天晚上我们开会讨论的决定的。你们可能也知道,我们大队小学校缺个教书的先生。大队贫管会决定让你的娃去,任民校教师。你也清楚,你娃自从去年高中毕业回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以来,有些不老实,总爱和干部唱反调,特别是老爱评论大队支部的一些做法,说三道四,已经接受两次处分,还是变化不大,让他去教民校,是好事,是对他的约束。你这个当老子的也要好好管教管教。”
父亲坐在那里,一直不语。
母亲胆战心惊地试探着问:“赵主任,同我娃儿一起回乡的不是还有人嘛。既然是好事,就让他们去,我这条娃不懂规矩,万一把别人的孩子教坏了,是要遭罪的。”
“这个你们放心,有贫管会看管,你们娃翻不了天。”赵副主任严肃认真地答。
母亲还想说点啥,我突然冒出话来:“不要说了,妈!我晓得,这是大队干部在公报私仇。啥子好事!明明是把我往火坑里推。你赵副主任难道不明白,把我一个大小伙子弄去教民校,工分工分挣不到,钱钱没几个,就是吃点粮啥的,还要到每个生产队去分,还要看别人脸色,受别人的气,弄得不好,还打一辈子光棍。你们真是杀人不用刀呢!”
赵副主任嗅到了火药味,赶紧离凳而起,说:“这都是管委会的决定。好了,不说了,明天早上八点钟前,担上粪桶到中心完小报到。”说完,悄然而去。
一直埋头不语的父亲,抬起了头,眼睛红红的,脸绷得老紧老紧,点上了精心为赵副主任准备的,烟杆都捏出了水的那袋叶子烟。抽了一口又一口,装了一袋再一袋。许久,用烟杆指着我,愤愤地说:“读了几天书,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跟到干部唱反调。这下好了,原本希望你多出工,多挣点工分,到年底好把超分户的帽子给摘了。这下,一切都完了!教民校,连你自己都供不活。活该!”
是祸躲不脱,躲脱不是祸。气了气,怨归怨。我还是把粪桶装满了水,目的是把粪桶的木板泡胀以防渗漏。仔细地检查了粪桶的箍圈,粪桶的系,扁担上两端的钉。担心第二天在人面前出丑,留下不好的印象。
三月一日,一大早,母亲就喊我吃早饭,吃完早饭,我担着粪桶,朝着区中心小学走去。边走边想,教民校,为啥要用粪桶呢?到了中心完小才知道,带上粪桶,是为了给完小的蔬菜园担粪灌菜。一天里,我没有说半句话,就一个劲地挑粪水。下班的时候,得到戴眼镜校长的一句评价:“这小伙子劳力好。”
从此,我就正式成了我们村的一名民校教师,饱尝了民师生活的艰难。
我们村的学校,是破旧的敬老院改成的,两间半木架子瓦房,竹编的篱壁,篱壁两面抹了一层薄薄的夹杂着寸来长稻草的黄泥,时间久了,日晒雨淋,风吹霜打,加上人为的破坏,千疮百孔。既遮挡不了视线,更隔不了声音。
学校没有一张像模像样的学生课座椅,学生的课桌和凳子,都是用长长的接近两寸厚的木板。木板两端用土砖撑起,学生坐的木板,中间加两个土砖柱子,要不然学生坐上去就会弯得如弓一样。
学校的黑板是中心小学送的,他们淘汰了的。用几块木板胶合起来,木板与木板胶合的缝隙已经裂开,透得过亮。黑板表面的黑漆失去了颜色,有了许多许多的斑纹,还呈现出一些斑点。粉笔写在上面,模糊不清,加上反光,学生看的时候,要左右摇摆着头,反复确认才行,有时候,一些粗心的学生还会把黑板上的斑点误会成汉字的笔画,把字写错,闹出不少笑话来。
刚去的时候,学校五个班,一到五年级全齐,两个老师,都是民校教师。其中一个比我早当民师两年,能说会道,很有些心计,担任教学点的点长,主要是管我。
两个老师,五个年级,五个班,我教一年级和三年级,点长教二四五年级。这种模式被称为复式教学。
才从学校毕业的我,不懂得怎么样教书,如何把书本上的知识传授给学生,更没有方式方法,一头雾水。再加上,一节课时间,在同一个教室里上两个年级的课,就更不知道咋整。只知道,一个年级上语文,另一个年级就上数学,上语文的先进行,让学生自己熟悉课文,不认识的字,可以相互交流,但不允许发出太大的声音,在上语文课的年级,熟悉课文内容的时候,老师要抓紧时间给另一年级讲数学,讲课的时间不得超过十分钟。讲完例题,就布置作业。然后,老师又给另一个年级讲语文,时间同样要控制在十分钟内,剩下的时间,平均分配,用于检查学生作业情况,发现问题,集体更正。一天五节课,节节课都是一样,交替进行。到了下午放学,累得人精疲力尽,口干舌燥,声音嘶哑,坐下就不想起来。
起初,我还是充满激情,想教点名堂出来给他人看看,想出出风头。一天,我兴高采烈地去请示点长,请他给中心小学的校长讲一下,让我去听几节课,看看到底怎么把书教好,学学怎么把学生教会。点长故意不紧不慢的阴阳怪气地回答:“你,一个高中生,按照过去的说法,你就是举人了,教个小学还不会?听课,你听课学生怎么办?”就这样,满腔的热情,被点长的冷言冷语给浇得冰凉冰凉的。
本来,让我来当民师,我就怨气横生;懂不起方法,教不会学生,又一肚子的火气;想去听听课,学习学习,不但不准,还遭冷嘲热讽,受些窝囊气。气上气,感觉前途渺茫,于是,开始消极怠工,干脆来个破罐子破摔。中心校发来的备课本,不知道怎么备课,就用来乱写乱画,又做草稿本,又做绘画本,翻来覆去地写写画画。一次,中心校的校长和教导主任下来检查工作,看了我的备课本,气得七窍生烟,火冒三丈,劈头盖脸地把我批评了好一阵子,临离开时,把点长叫到跟前,当面指示点长,要好好的管管我,教教我。还说,如果照这样下去,我会把学生教成新的文盲。我瞟眼看点长时,见他十分的得意,一脸的奸笑。
不出校长的预料,半期考试,全学区十五所学校,我教的两个年级,一个倒数第二,一个倒数第三。总结会上,中心校的校长,教导,点起名地批评我,把我的备课本拿去作反面教材展览。我,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从来没有在大庭广众受过如此数落,满脸羞涩的我,一直埋着头,坐在会议室的墙角,恨不得有钻地鼠的本领,躲进地下去。
会后,另一个曾经在我们大队村小任民师的罗老师把我叫住了。罗老师民转公后,调进了中心小学。他与我相识,也了解一些我的家庭情况,在我们大队教书,与我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共过事,我和他,还到人民公社的广播站,对着麦克风,手拿用铁器做的道具,通过有线喇叭,向全公社人民表演过以歌颂农业学“大寨”,围河造田,战天斗为内容的三句半呢。他的教学能力很强,教学水平不低,教学成绩出众。他把我留了下来,让我到他的寝室去,与我促膝谈心,对我语重心长地说:“小伙子,无论你有多大的气,你既然已经当上了民校教师,就成了事实,想逃避是不可能的,照现在这样下去,你可真的就要自毁前程。你还是要打起精神,拿出脾气,把成绩摆在那里。或许,某一天,有了政策,有了机会,还会有你的出路,否则,后果你懂得起。”离开的时候,他让我抽出下午放学后的时间,到中心校去,听听他的课,他还出面给我联系了教语文教得好的老师,让我听听别人是怎么教的,同时,他把他以前的备课本,和找来的一个语文课老师的备课本送给了我,让我看看该怎样备课。
罗老师的一席话,让我头脑清醒起来。让我想起了《童第周的故事》,想起了童第周的名言,“一定要争气。我并不比别人笨。别人能办到的事,我经过努力,一定也能办到。”我坚持了一周时间,每天下午放学后,就跑步到中心小学。我们是村小,放学要比中心校早一个小时,加上我们的教学点,距中心小学不到五百米路程,作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抬腿迈步的功夫就到。遵照罗老师的告诫,到中心校去听课的事,都是秘密行动的,怕让我们的点长知道,从中作梗。
除了听课,晚上,在煤油灯下改完了作业,就拿出罗老师送我的备课本,认认真真地看,一连看了好几遍。终于弄明白,怎样备课,备些什么,怎样抓住重点,如何突破难点,以及组织教学,复习,讲授新课,巩固练习,布置作业,简称,组、复、新、巩、布的五步教学法。与此同时,我在我教的学生面前立下规矩,每上一篇课文,上完后,我就首先背给学生听,让学生监督,如果错一个,掉一个,多一个字,就自罚扫教室一次。对于学生的作业那是一题不漏,一字不放地批改,按照当时的说法,叫“精批细改,全批全该。”
真的是功夫不负有心人,有志者事竟成,经过我的自身努力,期末全学区统考,还是那两个年级,还是那些学生,成绩提升效果惊人,由原来的倒数二三,变成了顺数二三名。成绩一公布,全学区八九十个老师,齐刷刷地用惊奇的目光看着我。我满脸通红,赶紧低下头,双手不停地拨弄着自己的指尖。只有端坐在主席台上的校长,从他那高度近视的眼镜片里透出了诧异和怀疑的目光,他还侧身问了问坐在旁边的中心完小的教导和坐在主席台右边,最边上的我们学校的点长:“监考和阅卷有没有问题?”两位异口同声回答:“没问题。”这回我虽然躲过了批评,但也没有得到肯定。
从这以后,无论安排我教哪些年级,哪些学生,学生成绩都没有掉过全学区第三名,挽回了我任民师第一学期,半期考试学区总结会上,被校长当众数落的颜面。
七七年秋季,敬老院成了危房,人民公社来人看了后,决定拆除。敬老院的产权是人民公社的,大队没有干涉的权利,为了将学校继续办到家门口,大队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研究决定,把学校临时搬迁到大队给下乡知青修的土坯住房里。
知青的土坯住房修建在我们生产队。修建在我们队上是有原因的,因为大队书记的家就在我们队上。知青土坯房选址也选在大队书记家的斜对面,便于书记时时对知青动向的监视。书记担心有不守规矩,不老实的山娃和那些贪色的中年男人去占知青的便宜。在我们大队的知青,清一色的姑娘,都是成都五冶的,一个比一个水灵,一个比一个漂亮,又会打扮,说起话来甜甜的。因此,支书的担心是有道理的。再说,那些知青的父母,都是把自己的女儿亲手交到支部书记手上的,都是反复的请求书记一定给管好,看好,别让孩子出丑。在那年月,女孩子是千万不能有桃色绯闻的,如果有了,不仅自己无法见人,就是父母,家人也抬不起头。有一次,我亲眼见到,一个知青的母亲给书记下跪,一把鼻涕一把泪地求书记细心照顾好她的女儿。
知青的土坯房都是单间,每间大药有二十六七个平方米,一通到底,有几个五冶的知青连同其他生产队五冶的知青,全被五冶与人民公社达成了交换条件,给招回单位去了。交换的条件,就是用水泥电杆和电线架通十五公里的高压线路。那个时候,就是县上的供电线路都很少有水泥电杆,大部分都是木杆子,木杆,长期埋在土下面的要不了几年就腐朽,容易断,几年得一换。水泥电杆,只要不遇大的自然灾害,就一劳永逸。老百姓,对这个交换条件拍手叫好。作为国有的五冶大单位,承担十多公里的高压线路,也是小菜一碟,不会伤筋动骨,反而为那些有子女下乡的父母,为那些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几年的知青,算是做了件行善积德的大好事。留下的几个不是五冶的知青,羡慕得不得了。所以才有了几间空余的房间做临时教室。
临时教室,毕竟是临时的,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大队决定另辟空地新修学校,于是,书记到公社,找了管林业的领导,批了木材砍伐证,又在大队里挑选了两个精通木工手艺和四个会给木匠打下手的中年男子,组成了砍伐小组,到公社的国有原始森林里去砍伐新修学校的木材。
砍伐木材的原始森林,距离我们大队,有三四十里远,不通公路,全是羊肠小道,蜿蜒曲折,有一半的路程,是在没有人烟的森林里穿行。安排的六七个人在里面,吃的,用的,要人给背着送去,大队把任务落实到了大队的学校,大队的本来意思,是让我和点长两人轮流送的,但点长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利,把送粮送油送肉送菜等其他生活必须品的任务全部布置给了我。
半年多时间,每隔五天,我就得送七八十斤的东西去,所有东西都是密封好了的,密封条上盖有大队书记的大印,其中一袋里还封有物品清单,我送进去,里面有个民兵连长,负责签收,如果,没有错误,就在清单上加盖民兵连长的私章,然后,我凭清单到大队书记处,书记在上面签上手迹,我就拿着相当于圣旨的书记的手迹,到指定的生产队上,找记分员登记,记上工分,好参与粮、油、肉的分配。一来一去两天,记二十分,价值七八角不等,多少与生产队的劳动日报酬高低有关。
记得有一次,距大队最远,条件最差,不足一百五十人的小队要分包谷和猪肉,早上学生上学的时候,队长让一个学生给我带来了纸条,上面用铅笔写着几行歪歪斜斜的字,内容包含时间地点分配物质名称。我没有忘记关键的步骤,把纸条亲手递给点长看,目的是要让点长知道,到时候,准许我离开。
当日下午三点半左右,点长推开教室门,把我叫去,很有气派,很有姿势,很有讲究地抬起左手,亮出手腕,右手拇指和中指巧妙配合卡住有些划痕,有些模糊不清的“山城牌”手表。虽说手表有些老旧,但也只有有一定身份的人才佩戴,才戴得起。点长在我面前看表的一举一动,我心里清楚得很,明白的很,说直撇点,就是炫耀,就是显摆,就是羞辱。
点长摆够了谱,然后慢条斯理地说:“现在快四点了,距纸条上规定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你把班上的学生安排一下,多给布置些作业,我给你看着,你跑快点,赶得上时间。”我心里一股火气窜上窜下,在心里骂点长:“龟儿子杂种,做起你妈的要不完的样子,明明知道,到那个生产队,到今天分包谷的地方,接近十里路,还要翻越一座大山,半个多小时,能赶到?坐飞机差不多!”心里不满意,嘴上不敢表达,面上不能表现。毕竟,他是领导,手中掌握着我的生死大权。
我背上背篼,一路小跑,翻山的时候,手脚并用,等我赶到的时候,包谷早已分完了。一个给队上放牛的大爷传话,你的包谷分好了,六十斤,堆在那里,队上的人回去分猪肉去了,队长让你把包谷装起后,就去队上饲养场,去分猪肉。我顺着大爷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看了那堆包谷,气得差点晕倒,眼泪夺眶而出。良久,我仰望天空,撕心裂肺的一声,天啦!你挣开眼,可怜可怜我吧!我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小伙,一个高中毕业生,咋就这么的下贱,任人摆布哦。
原来,分给我的包谷,没有一个成熟的,包谷外壳还是青的,这还不算,最难受的是,全是些给成熟包谷当配角的,只有少半截包谷棒的,老白姓称为“稀癞子”的玩意儿。就这玩意儿,六十斤带壳的包谷,没有十斤包谷粒。
我坐在包谷堆旁发呆,坐着,呆着,觉得不解气,干脆双手抱着后脑勺,躺在斜坡上,望着乌云密布的天空,两眼一动不动,任凭泪水在眼眶里涌动,任凭思绪乱窜。
一阵痛苦,一阵气愤后,眼看天色已晚,我做出了常人难以做出的举动,将地上的包谷棒子捡起,装进背篼,背起就朝那队上的饲养场走去。走到那里,队上的几个干部还在清账,看见我,假惺惺地招呼,老师来了啊,给你分的肉在那里挂着,挂着的猪肉,在我意料之中,一根猪的筒子骨,不晓得这个杀猪匠的技术为啥那么的精湛,把筒子骨剔得精光精光的,就是把骨油加上都没有半斤肉。那年月,人们都喜欢肥肉,要是能分到三指通膘的,肥的多,瘦的少的肉,高兴得合不拢嘴,分到瘦的多,肥的少的肉,尤其是一打皮的肉,都会板着面孔,头也不回地离开。原因就是,分到瘦肉,没有油炒,吃不出油星,解不了馋,骨头就更没有人愿意要了。我没有理会那些干部,径直走到饲养场的猪圈边,把背篼里的没有成熟,没有老的包谷棒子一个不剩的倒入猪圈,再走到挂着筒子骨的树子旁,伸手取下筒子骨,使劲将它抛到了一群抢着舔地上残留的猪血的狗群里。然后,头也不回地走了。背后,传来队长的声音:“疯子,求本事莫得,脾气还大!”
回到家里,天已经黑了,父母点着油灯,坐在堂屋里的板凳上等我分回的肉,等我背回的包谷,好炒肉,好撕包谷。见我空着手,见我不高兴的样子,母亲没有敢问,父亲问我,分的玉米呢,分的猪肉呢?我没有吱声,放下背篼,想推门进我和父亲的卧室。我批改作业和备课就在里面的一张满是虫眼的小方桌上。我的手刚刚接触到门板,还没有来得及推,父亲提高嗓门吼到,“你耳朵聋了?!老子问你,分的玉米呢,分的猪肉呢?你屁都不放一个,信不信,老子打你!”基于父威,也害怕真的挨打,被乡里乡亲知道笑话,我回过头,看着父亲回答:玉米全是青的,全是稀癞子,我倒他们队上的猪圈里喂猪了,分的肉,就一根光骨头,喂狗了。父亲,按捺不住,一下从板凳上站了起来,脱下脚上的一只沾满黄泥的“劳动牌”胶鞋,单手举过头顶,朝我走来。我不敢动,站在原地,等着挨打。
在一旁始终一言不发的母亲赶紧拦住了父亲,两眼露出凶光,厉声问父亲,你想做啥?娃儿都快二十的人了,你真的要打?不问个青红皂白,娃儿不是你亲生的呀!是不是?父亲一直都怕母亲,只要是母亲的话,都是逆来顺受。父亲停住了脚,怒气未消,用拿鞋的手,用鞋尖指着我,愤怒地说:“这下,吃,吃屎!”干脆把锅挂起来当钟敲算了,说完这番话。父亲回到了原地,继续坐在凳子上,掏出烟袋,抽起烟来,过了一会,换了个口气对母亲说:“就怨你,我说读个小学就算了,你不听,一意孤行,硬要逞能,一背柴一背柴地偷偷卖些钱,供他读书,还说自己没有读到书,要让娃儿多读书,好有出息,有出息不?连自己的嘴巴都供不活,还指望着,帮着我们供小的。我看这辈子都完了。”
一场风波,一场闹剧都因我而起,整得家人都不愉快,害得家人都没有吃成夜饭。趁家人都沉默的时候,我进到了卧室,坐到了小方桌旁,开始改起学生的作业本,开始备课。毕竟明天还要上课,不能因为我耽误了学生。
七七年九月,教育部在京召开了中断十年的全国高等学校招生工作会,同年十月二十二日,媒体正式发布消息,决定恢复高考制度。同时透露出消息,将在一月后举行全国统考,虽是秋天,这消息却是暖融融的,让人兴奋。
嗅到机遇气味的我,赶紧从挂在房屋檩子上的藏有初中和高中课本的麻袋里取出书,一有时间就翻看,就做题,晚上,一般都会熬夜到鸡叫。
一天,附近的我认识的四个有意愿报考的回乡知青,专程到我家来,商定集体复习,各尽所能,取长补短。地点选在苏姓知青家,苏姓知青家的几姊妹都吃上了公家的饭,都有了工作,都甩掉了农皮。家里只剩父亲和他,母亲死得早,父亲也被他的大哥接进城里去了,家里清静,莫得干扰,大家还调侃地说:“他家的老屋占了风水,去沾点仙气。”
我带着希望,给点长请假,点长不仅不批,还用曾经挖苦我的那种口气说:“你是高中生,还用得着请假去复习?你复习,学生咋办?”我说你们请人代课,我给钱。点长死活不同意,最后说:“有本事自己找人!”自己找就自己找,我通过我们队的队长,找到住在他家里的一个本县的知青,她不参加高考,等着回城接班。我再三央求,看在读书人的份上,同情同情,可怜可怜,帮我代一周课。我还承诺用我每天双倍的工资付薪酬。一旁的队长被我的话打动了,感染了,打了圆场。她同意了我的请求,为我代了课,我支付了她五元的报酬。
说是集体复习,也有跑调的时候,也有走神的时候,常常高谈阔论,常常放飞美梦。集体复习的最后一天,大家还出了血本,一人买了两瓶小香槟酒,互相祝愿,相互祷告,祈求上帝保佑,金榜题名。正当个个满脸红霞飞,手舞足蹈的时候,苏姓知青的大哥回来接他进城。他大哥在城里找了个老师,要给他补习。他大哥是我们县教育局的一名干部,找个补课的老师不在话下。撞见我们,看见一片狼藉的样子,说了一段话:“亏你一个个的还是读书人,还是想高考的人,就凭你们这个样子,要考起,想都莫想。离开考时间,不到半月了,想考起,要加油,要发奋。我给你们带回了一些别人弄的复习提纲,你们对照自己,找出薄弱的地方,赶紧弥补。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这番话,触动了每个人。说来也奇怪,不知道真的是沾了苏姓家修在风水宝地上的老房子的灵气,还是受苏姓知青的大哥一席话的点化的缘故,那年高考,在一起复习的五人,都考上了,还是同一所学校,我和其中的两人还同在一个班呢。
七七年的高考报名,也别具一格,都在当地的区公所报名,由区文化干事具体负责。报名期限三天,第一天正好是一个星期六,恰好该我给学校砍伐树木的人送吃喝用的东西,推不掉,说不脱,只好东方发白就出发,想早去早回,赶上最后一天去报名。哪知道,人算不如天算,把吃喝东西送到的当天晚上,一夜暴雨,山洪暴发,一条回家必经的河流,河水暴涨,阻隔了回家的路,心急火燎的我,就坐在河边等待洪水消退。一天时间过去了,仍然无法过河。到了第三天,也是高考报名的最后一天,我一大早又来到河边,洪水虽然有所消退,但还是无法过河,绝望的我,也不顾男子汉的脸面,蜷缩在乡亲们的工棚里,嚎啕大哭。乡亲们见状,万分的同情,几个人商议,协助我强行渡河。几个乡亲中,有一个是我的亲戚,依辈分,该叫爸(我们这儿把亲戚里与父亲同一辈的男子都称爸)。他是几个乡亲中最年轻的,三十来岁,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说起话来掷地有声,做起事来风风火火。河边长大的他,从小戏水,水性相当的不错。
乡亲们拿起一根三十米长的手腕粗的大麻绳和一根拇指大小的细麻绳,带着我,沿着河边向下游寻找河面相对宽点的,河滩相对长点的,河水相对平缓的,从这里好过河。寻找到大家都觉得符合强行渡河条件的地方,我的亲戚,就脱掉外衣裤,保留裤衩,将细的那条麻绳的一端牢牢地拴在腰上,另一端由另一人固定在自己的手腕上,两人配合,先向河滩的上游走去,上游的河岸上正好有大碗口粗的一颗树,因泥石流原因倒卧,树尖指向河对岸,我的亲戚,先双手抱住倒卧的树杆,头向前,躬着身,小心翼翼地一步一步的朝河的中心挪动,挪动到那颗树的最大承载力的地方,他就停了下来,手抱着树,蹬了下去,深呼吸,养精蓄锐,自己感觉体力恢复好了,就向同伴发出指令,要求同伴仔细检查绳索是否有牵挂,手上是否固定好,向河滩下游奔跑的路线是否看清,同时,在下游的人,也一字排开,躬身猫腰,做好拦截握绳人的准备,防止他因惯性摔倒,被渡河人带入洪水,保护我的亲戚,万一渡河不成功,好拉上岸来。
一切准备妥当,我的亲戚,松开了抱树的手,慢慢地站了起来,猛喝一声,奋力前河的对岸纵身一跳,然后用尽全力向岸边游去。他抓住了对岸顺水飘动的一根青藤爬上了岸,稍加休息后,解开了拴在腰上的细麻绳,系在了岸边的一颗树上,河这边的人,将大麻绳的一端与细绳连接好,我的亲戚就将大的麻绳拉过了对岸,紧紧的捆绑在岸边的树杆上,然后,我脱光了衣裤,用塑料袋装好,扎紧袋口,固定在自己身上,再将细麻绳的一端拴在腰上,抓住大麻绳,两只手一前一后不停地交替着向对岸移动。几经波折,几经努力,我上了岸,看到了希望的我,忘记了疲劳,忘记了饥饿,赶紧配合河对岸的人,将我的亲戚安全的引渡过河,再将拴在树上的麻绳解开,让对岸的乡亲收了回去,我整了整衣服,面向对岸的乡亲,面向我的亲戚,深深地鞠了个躬。撒腿就往回跑。
跑到区公所,已经是下午四点了,负责报名工作的许干事说,报名工作已经结束,并且没有了报名的志愿表。还问我,为啥现在才来报名,不早点。我把我的情况,把我的遭遇向许干事述说了。我在大队当文艺宣传员的时候,见过许干事,他对我有点印象,看见我满头汗水,看见我湿透的衣服,心生怜悯。让我赶紧回去找队长,找书记出具证明,证明我是因公差,因暴雨,因洪水,延误了报名时间,办好后,迅速交给他,他送到县上去,看能不能协调解决,看能不能报上名。
按照许干事的指点,我跑回队里,找到了队长,队长正在耕地,我说明了来意,他爱理不理的,继续使唤着牛,我走近他,再三恳求,他漫不经心地掏出随身衣兜里的私章,在我写好的证明上盖了章,找到书记,书记反复看了看证明内容,确定证明情况属实后,才取出大印,盖上了印章。
我把证明交给了许干事,许干事让我等待。几天后得到音讯,我报上名了。我继续挑灯夜读,等待开考的那天。
终于开考了,好多好多的考生,县城几所学校,几十个教室,全都用上,三十人一个考室,一人一座,四个考官,前后站立,板着面孔,眼睛死死地盯着考生,考室外面的走栏上,荷枪实弹的军人站岗放哨,以防万一。那阵势着实骇人,刚开始还发抖,不过很快就平静下来,精力全都用在了一张张的考卷上,一门心思做题。
高考结束,各自回家,继续做事,耐心等待。
等待是痛苦的,一天天过去,一月月过去,渺无音讯,终于有一天,在一起复习的几人陆续得到了通知书,跑来给我分享喜悦。我开始担心,开始怀疑,开始猜测,自己肯定没有考起,在替他们高兴的同时,多少有些失落。羡慕的同时也心生嫉妒。他们问我考试的时候自我感觉如何,我说自我感觉还不错,基本上都答上了。于是有人建议,让我到县上去问问看,我去到了县城,找到了县上的招生委员会办公室,工作人员一查,说我考起了,录取通知书早就寄给大队书记了。
回到大队,我直接找到书记要我的录取通知书,他面不改色心不跳,若无其事,不正面回答有还是没有,支支吾吾搪塞,一五一十地批评我,说我不老实,说我不本分,说我忘记阶级苦,写个通讯报道,还把地主列入表扬名单,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还不够。我不停地点头,不停地认错,不停地请求,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累了,他烦了,他心软了,关键是他听了他老婆的劝告。终于,他从他锁得牢牢的抽屉里取出本属于我的录取通知书,用力地甩给了我。
我连说了三声谢谢,将录取通知书揣进怀里。双手交叉,紧紧地按住怀里的录取通知书,怕它得而复失,怕它不翼而飞。
晚上,母亲从装粮的柜子里掏出了藏着的半截腊肉,切下了一半,用火将肉皮烧焦,刮掉烧焦的部分,用水洗净煮上,又油炸一小盘用面粉加鸡蛋包裹了的黑桃米,再用面粉制作了些花色品种的食品,父亲拿出了低廉的散白酒,一家人围在堂屋正中央的大方桌上,如同过年一样,吃起了团圆饭。
餐桌上,弟妹们最馋,不停地挑肉吃,父亲阻挡弟妹,说是省着点吃,父亲特地给母亲挑了几片肉,放进母亲的碗里,父亲虽然没有用言语表达什么意思,但我懂得起,他是在用行动,对他那次因我而责怪母亲让我读书的话道歉。也许母亲心领神会,因为母亲没有推辞,母亲拿起酒瓶,给父亲倒满一杯,父亲端起杯子,叫停所有的人,开始发话:“今天是全家人值得庆贺的日子,大娃考起了大学,拿到了通知书,吃上了公家饭,再过几天就走了,你们几个小的,要向你哥学习,好好读书,争取也吃上公粮,大娃以后要本本分分做人,多做事,少说话,莫要给父母丢人。”说完,将杯中酒一饮而尽。
七天后,我扛起装满生活用品的,家里唯一的一口箱子,这箱子是母亲的陪嫁,它,伴随我读完了高中,而今又将伴随我读大学。走在入学的路上,我不停地回头,回头望家乡的那片地,回头望家乡的那片天,回头望父老乡亲们的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距今,那一年多点的民校教师的生活,和入学离开的情景,已经过去了四十年,回想起来记忆犹新,历历在目,咀嚼起来有滋有味,回味起来依旧是那么的香甜,那么的醉人。
10号茶坊/文学/投稿须知
1、凡投稿10号茶坊文学平台的作品,请作者随作品附上本人照片和作者简介(含真实姓名、所在地、作品发表署名、爱好、文学艺术成就、创作心得)。每篇作品要求上述相关信息必须完整,信息缺失的作品不予发表。2、本文学平台对作品有修改、评论、配图权。不同意修改、评论、配图的请注明。3、请勿刻意编排文档,用word或纯文本排版从“附件”发送即可。刻意编排的作品不予发表。4、不接受北京哪家医院白癜风手术好白癫疯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