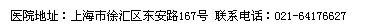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聋症 > 聋症病因 > 海派诗人诗刊创刊号正文五
海派诗人诗刊创刊号正文五
第四栏目责任编辑∶宋文静
现代化梦境外二首/佳枣(复旦)
我喜欢英文译名,并因此感到羞愧
直到他同意走进,安慰我一种西方
确乎如此的高贵性
尤其在地球上遵循先到先得的定理,飞到
高空也算么
(而我所疑惑的是他究竟什么时候飞上了天)
最后还要多虑地找他真正的嘲笑表情
也是到我最后发现的,那种新型的尝试
可以找到玻璃罩和电影放映机的现代化工厂
据说,到目前为止还是据说
工人可以根据笔迹判断一个人的心情
为什么说是传闻,这也不难
理解嘛!
如果需要一种反馈(类似影评)
啊!
如果需要一种反应,
无论这玻璃房需要什么,除了军事知识
像我和他之流,话说得比你们多
这是一桩悬案,在我十八岁来了天津
看到铁笼子轰地笼罩
看住我
大概女性是最聪明的,西方女性不必再说
在此时住了许多个似他的病人,他也在和我
一起判断,从玻璃房里透出的哪些
是焦虑的,或是安静的
赤十字
他有一个读小六的妹妹,戴黄帽子上学
散步的杉树,种在中学里
可以让他几近消失的肩膀微微脱臼
折叠好放入盒子,被朱鹮叼走
不同于小时候,最近他不再怎么怕红脸鸟类
大概是有了一些新的兴趣
找到妹妹鼻尖到嘴唇连线的正中央
那颗痣的风味,很像妈妈
“朱鹮鸟飞回来啦!”
背着书包洗碗的妹妹大声叫出来
写下小题板上一个大大的赤
他看得出了神,想起平假名里还是“を”(wo)最难写
夏天正午看到妹妹一段光洁的人中,还有津津的汗
到了十五岁,可别去给肚脐开洞啊
妹妹抿嘴笑了笑
像极了客厅里挂着的某副浮世绘
不如归去
时间不知被谁犁过,松松垮垮。
春耕的鞭声一下下敲打着过路人的神经。
田垄上伫立的人啊,
你不知道你的斗笠在我看来有多么神气。
很久没打草,根根灰绿已经太高,
团团地绕住我僵硬易碎的膝盖。
一步一绊,我分明地感到来自大地
蓄意而沉默的牵扯。
可是盛大的日落还要进行。
我在草堆里踉跄,追逐太阳,
哭着扑倒在阴凉的土里。
而思绪还高高地立着,
一时间竟长得比草还高。
姐姐外二首/吴径(复旦)
姐姐,昨天你重复了我的话
我想我们认识得还不久
姐姐,我想出去跑步
感到自己的肠胃四季如春
而整一条街的哺乳动物都畏惧我
姐姐,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想我做得已经不错,你教给我的
心肝脾肺肾,总让我在生人面前
感到骄傲,姐姐。我们不能断裂一天
我想,姐姐,我看到你,
你怎能比我还小,比我还要开放
门道
做为内行人,我必须指出,
田小姐的服务远称不上尽善尽美。
热情的微笑里一种大观园式悲剧
在有意赤裸的十趾上幻现,直截了当。
古龙水,剃须膏,假模假式的谈话
紧随其后,口舌交锋开始且不留余地:
“想什么呢?最近过的还好吗?”
她继续卖力工作,换来我的置身局外,
称之事件,好像有些夸张——不过,
事件进展并未出现恶化亦没有好转。
完了事,田小姐倒上半杯白兰地,
这令我意识到,她的部分癖好并未痊愈。
早先的三等货如果坚持出来现世,到如今
就能充一流品。对此她绝不自夸。
田小姐终究用浴袍代替了西式服装,
而我则坚持反对没有憎恶的玩乐。
我捏捏她的双足,哦,她真醉了;
媚眼勾魂,这种诱惑着实令人腻味。
装作掩饰某种羞愧,我告别田小姐,
像样地走到街上,想着刚结束不久的会面。
所有高洁的正经者都鬼祟得渐入佳境,
进言之,是摸清门道前必经的历练。
罐头装金枪鱼
我决定游泳,在整整九个月后。
两周内,将有女孩邀请我作伴泡温泉。
一点五公里的路显得没完没了,
每次去健身房都有这样的感觉。
我是突然走的,走进小区的绿化里,
看着影子在身后不断拉长。
地产中介的招牌开始变暗,
前方小吃店轮廓还不很清晰。
我希望手边有一个掌上电视机,
用调到最响的天气预报,
缓解步伐加快的狼狈。
前台小姐的一声问好(外地口音)让荒谬感袭来,
成功将附着于会员卡上的怯懦攻克,
脚趾裸露在人字拖上,悄悄地随着音乐晃动,
突如其来的大汉打破了这种节奏。
因为有过一面之缘,他小心翼翼地暗示我的肥胖,
我呢,我笑着说,我顶讨厌他用的香水类型。
对话无法进行下去,紧张感吹弹可破。
最后,前台小姐解了围——或许是看不惯,
本地又长又慢的对峙方式,且难以打发。
进水管坏了。那什么时候修好?我问。
明天。这是一名矮个子救生员。
黝黑的皮肤炫耀着他是如何认真地工作,
室外泳池的关闭让他失去了用武之地。
我不愿表现地游离在大妈妈的救身圈之外,
于是发现快速泳道因两对情侣而支离破碎。
女孩会说,有很多男生发起攻势。
评估正在展开,权衡还在继续。
怎样进行有力而不失体面地竞争,
将会是重要的——显然不唯一的
——考核标准;如何避重就轻地周旋,
将会是主要目标。你到底游泳吗?
十岁(也可能是十一岁)的小男生问我。
他示威地划了两下水,又重复了一遍。
我被这极端的动作震慑住。事实上,
我早就因过高的人口密度而惶恐不安。
身体要擦干,否则容易得湿疹,有人总结道。
我急吼吼地跑回更衣室,假装自己有浴巾,
在年轻爸爸的小女儿面前赤身裸体,
——喂,请不要踩我的人字拖好嘛?
剧场外二首/张极泰(复旦)
我要面对观众塞上耳朵
我听不见掌声
嗅不到烂菜叶和霉味
抑或雌性毛孔分泌出汗液的香
我把头钻到舞台下面
钻进魔术道具和老鼠的窝棚里
我亲吻地面,与蜘蛛对话
给它们介绍烹饪技法
它们向我讲述闪电击破云层
雨水怎样降落到家门口
它们饱餐一顿
它们还说:
“丁香花香启三钟儿
天兽昼袭世间
六世祖率族出老宅”
蛛丝儿谱出家史
先母如何以血肉成全子孙
长螯羫力搏穹涯猛促
从此成全八代无战事
我听不懂吟游诗人的歌谣
正如鼓掌的观众
之于幕布背后的故事
然而五百年后
在皮影烧成灰烬的时代
当地面上尘土吐出晨光
幸存的人互相依偎
纵情歌舞的技法
重新显现出剥开皮肉的心脏
花生大叔
我要面对观众塞上耳朵
我听不见掌声十块钱一袋儿,
沾满烟灰与痰渍的金属托盘儿,
“吃,吃,吃!”
硬座火车上实在豪爽。
“南京热,
还是达里尼气候好。”
渔船满载鱼虾,
天下最好的羊汤,
大旱百年不遇,
玉米在满山地缝中渴死。
凌晨三点钟。
邻座单身女郎搂着女儿睡去。
“你是哪儿的人?”
“红房子。”
“寺儿沟?”
“关东署,办公楼。”
“大衙门抓了放火团,正修牢房呢。”
门前草坪收割整齐,
队列方阵砍去头颅。
绿色的长官牵着东洋大狗。
“我家在大菜市搭窝棚。娘捡了烂菜叶熬汤。
后来搬进房子里,地板下抽出一把开刃大刀。”
“哈,你说南山?
南山啊,现在都是私人会所。”
“昆明湖,不是军属房吗?”
“什么啊,男男女女!”
说着便呛出眼泪,鼻孔喷出两道二锅头。
“州法院放枪,我逃到春日小学校。”
“不如去老虎滩。沙里挖蚬子,能熬一锅鲜汤!”
“噢?台风夜袭化工厂那天?
“对,我亲眼看见,
狗子穿着晚霞子,站到面包车上。”
“小胳膊拧不过大腿!”
“敢放火的都是英雄!”
我蹲在条幅底下烧纸,还扯坏它一个角。
“不让烧纸了。不让。”
“不让你吃饭你吃不?”
“哪个不要命的敢吃大米饭!”
“要我说,真去放把火?”
“见识过。火车头的煤炉子里,也有几块酥骨头。”
“那些人的骨头是硬的!”
“硬的?冲进马葫芦盖儿里,死得莫名其妙。”
我低头不语。
其实他不知道,太庙里供着生石灰。
晴天那夜,天火来袭。
讲题
小查给大家讲题。
没有人听。
所以我不讲。
我把作业本埋在山崖上。
种上松树苗,培上土。
五百年后,我看到有人摆香炉。
还有人摆地摊,
卖红丝带和铜锁头。
纸张烂在地里,化成树的汁液,
一直涌到叶子末梢,
涌进仓皇下落的太阳里。
买锁头的赚到钱,
拿去炒股,
拿去生产对二甲苯,
用来囚禁地平线上的余晖。
而小查仍在讲题。
他在三里屯商业街讲。
他去对二甲苯工厂的门前讲。
他还去广场上讲。
广场上的人们别来无恙。
监视者外一首/蒋瑶瑶(同济)
他不是演员,却有了一个观众
黑暗里的眼和耳,比他自己
更了解他
监视器里的生活确凿而安全——
早晨,钟里跳出布谷鸟
将他从梦中唤醒
杂乱的胡须未经梳理
恣意如热带的草木
嘀嗒作响的,是打字机的呢喃
掌纹抚过按键,嘶吼便喷薄而出
红色的墨水旋转跃动
被禁止的舞蹈总是格外迷人
若钟声划过窗口,便和衣而眠
枕着恰到好处的爱意和
些微的逾矩,仿佛偷到果糖的孩童
又甜蜜、又忐忑
观众的存在,是一个秘密
了解他的一切。了解
便可以毁灭
无数故事曾被这样终结
但他突然想听
不是以眼和耳的身份
扳机被叩响
枪膛里的子弹
下一秒,便将呼啸而出
方向却对准了自己
金属钉入骨肉的一刻
耳边响起了永不背叛的誓言
儿童节的草坪
儿童节的草坪格外热闹
花皮球滚过鲜嫩的草地
一群白球鞋撒欢儿地跑
衣摆带着风,吹起了
石桌上的几页纸,和
坐在长椅上的裙子
浅睡的白猫也被惊醒,一蹬腿
跳到秋千上。有顽皮的
轻推一把,它们就一同
起飞,朝着刚刚升起的风筝
旁边,跟风筝一样大的太阳
慷慨地撒着亮晶晶的糖
金色的雪松下,一个孩子半躺着
铅笔在白纸上勾描——
长耳朵、短尾巴、红眼睛,还有
发光的角正被安在前额上
“兔子没有角。”从天而降
指节分明的大手笑着说
小小的头摇成拨浪鼓
“这是云。”
“但是今天并没有云。”
“明天的云。”
低声咕噜,像鱼吐着泡泡
眼睛里有蝴蝶扑闪翅膀
此刻,社交网络里正在进行狂欢
以节日的名义,消费和缅怀
然而哪一天没有晚宴举行?
这样的日子,我只想
半躺在草坪上,看一只
长着角的兔子,从空中飘过
直到黄昏
直到身上落满灰尘
生活的感觉(组诗)/吴彦哲(同济)
幸福
在集体的阳光下
我们一起慢跑
阳光过后
树上挂着许多奶绿色的葡萄
只有我一人
看见了这些丰满的月芽儿
一定比幸福更甜美
理智
我会在合适的时候离开
就像蝉脱离他的壳
一次一次
盛满了夏天的阳光
合适的时候并不多
需要你耐心等待
而生命中很多时刻我们冲动
一朵花抢着夜间开放
在黎明到来前便死去
我并不是牢笼。我是衣服
活着常常会感到无奈
又不得不穿上它
在雨下
雨水充沛我在雨下
我和雨的秘密谈话
正背着植物进行
“雨又不说话,
我怎么知道是在
爱我还是嘲笑我。“
雨水带来土地
雨水带来私语
一颗湿漉漉的心
赶在回家前下雨
雨我头顶的
是神碰杯时洒出的酒酿
在雨上是云
看到思念像头发一样生长
在雨下是我
头发润了
蜷缩成子宫
卖橘子的人
卖橘子的人晚上
就睡在摆橘子的木板上
白天橘子就睡那儿
他先把橘子卖给别人
又接着把自己
卖给了夜晚
和一天比一天寒冷的日子
而寒冷更深的时候
卖橘子的两口子围坐在一起
身旁的橘子都烧起来
数树
这儿有好多树子
四个四个数就是好多把椅子
两个两个数就是好多双筷子
一个一个数看见树上分叉着
许许多多受难的耶稣
我们的人子
扇子的历史
追溯到风生
风起
风落
一段感情就这么结束了
冬天
街上到处是黄色的传单
冬天深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抗议
被我长久的无视或许他们急切的诉求
只会让季节越来越沉重
还有好多事情要做。
还有好多错误永远无法改正
一片忍无可忍的枯叶爆炸了
然后落下来静静轻轻我在空腔中心
听到那绝望而肯定的回响:
冬天深了
乡村记忆外二首/张振(江南)
黑夜切断眼睛回家的路
心灵骑上黑马探寻归途
青灰色的瓦房寂静无声
任由伤感的夜色蔓延
衰败的牛栏反刍的声音
陪伴孤弱的油灯光芒
深井堆满了摔烂的叶子
微微地喘息童稚的呼吸
桂花清香的隐忧
对崩溃的麦场一无所知
许多漂泊生命的沉沉结局
诠释青春燃烧后的故事
飘进另一种贫匮的记忆
月亮跳起自己的舞蹈
屈服于自我的旋律
泪光浮贴在守护麦田的树上
闪烁石磨推出的天机
乡村反抗罂粟般的睡眠
思念风夺去的死者
辽阔的影子逐渐放弃存在
小心地躲避一个个噩梦
似乎找不到有借口的错误
残忍的谎言永续地轮回
星与星变奏的安魂曲里
破碎的黎明热切地涌动
在时间的遗址上点燃玫瑰色天空
寂灭的河流
我在寂灭的河流
捞到早逝者
为尘世祈祷的微笑
月亮弃落
在水中的黄金眼睛
闪耀出汽车狂热的嚣叫
与玫瑰家族
争夺领地后的愤怒
一阵必然的风吹来
把似乎永固的镜面
砸成一块又一块
木偶般的碎片
石桥跨越河面的昏暗
连接隔着世纪距离的路灯
飞蛾以古老的旋律
绕着灯光忠诚地旋转
不在意焚烧自己的火焰
是否突现
一条镶满玉块的鱼
从窃窃私语的水底跃出
音乐瞬间绽放
惊伤夜的死寂
搅动的细小的漩涡
引起周围高楼庞大的示威
柳条抓住漂流的星星
设立此岸和彼岸
不断重新开始的标志
运送白昼尸体的道路
呈现给河流
五颜六色的送葬人的足迹
晦暝的树林中
升起猫头鹰笛声
扩大空气生与死的范围
注入木舟眩晕的想象
墨黑的叶子
高傲地对黄土说:
“玉玺无限的权力。”
“时间最终回归的梨形轮廓。”
黄土对树根回答
堤坝看到自身环形的影像
仿佛试图完成的残缺的圆
为了在新的注视下生存
自己塑造万花筒般的表情
游过世界的浮云
在深夜凝聚成
有斑斓图像的水波
里面有许多孩子蓝色的目光
尝试构筑向日葵天堂
里面有海洋分派的手势
安排匆忙游子合适的归房
浪花在石头上
雕刻出历史永远陌生的碑文
也许只有殉道者理解
河流占据我的全部预言
永动地继续今天的远程
怀想
一
窗外哭泣的微笑
最终被这个世界抛弃
为了纪念地下走动的死者
月亮以孤独的姿态
照耀迟缓的我
阳光下风的灰烬
偎依在黑夜敞开的坟墓
年轻逝者的歌声
成为让树林感动又易忘的主旋律
深不可测的反影
溶解在企图新生的星空里
迫使我以及其他旁观者
转变为夜的亲历者
像星星一样
在黑暗处仰望
二
夕阳的伤口
从未想过愈合
余晖的轰鸣
震撼每一只茫然的喜鹊
街道秩序井然地走向
尚未成为黎明的预示
也许是倾心于黑暗的天空
将你无情地放逐
没有思念,没有吊慰
万盏灯火无所事事地消耗生命
只有落叶睁开眼睛
能够看到消逝的地平线上
骑士隐隐约约地涌来
遵从世人无法听到的召唤
三
属于诗歌烈士的黄昏
把你收留
于是已经堕落的太阳光
再一次在深渊燃烧
然而光只为少数心灵所洞察
夸父的遗骸似乎正在追逐
最后的光的残片
这篇神话
无法在这座悲伤的都市照耀
有着永恒渴望的风
被无数的大街小巷进一步扭曲
青铜色的梦
从此找不到静默的上空
听不到你恢宏的脚步声
没有你的存在
整个世界便沉入逃亡般的昏睡
四
庭院落满了月光的阴影
试图抓住游移的常春藤
杨树坚持保留夏天
残存的热情
风在葡萄间静静地流逝
感受着羁绊和愉悦
构筑季节成长的通道
啊,多少人渴望得到过去错失的收获
作为现在对未来的变奏
你留给我的回忆
维持最初之梦的燃烧
夜给予众生的伤痛
却未曾减弱
龙的图腾,鱼的传说
你未曾持续地形容
在你的左眼和右眼
开始和结尾找到了归宿
又留给我一个单调的夜晚
初迎新生
/刘潇潇(江南诗社皖鸢诗歌小组)
尤记去年此日中,映阶桃李笑秋风。
虹桥落影花津渡,杨柳垂青稷下宫。
书箱莲子一般绿,人面林花次第红。
笑语盈情今又似,当时回首总迷懵。
倦寻芳慢?乙未中秋/姜燕(江南)
且循径往,闲伫秋林,阶磊亭煦。
罢饮荷杯,又把菊英枫露。
芳草天涯春渐老,少年知己安如故?
倦黄昏,拚醉榴裙舞,月移星幕。
惜良夜,何寻乌鹊?
皎瀚浮槎。清浅谁渡?桂斧檀弓,孤酒悔情相误。
幸别山河依有约,君思常念常相诉。
愿轻忧,寄灵风,静香一炷
雨外一首/卢文韬(江南)
不经意间我们的城市又下起了雨
可惜你已经过了踩水的年纪
也学会了挽裤脚和面对溅起的积水时
保持着好脾气。脚趾间隐秘的疼痛
提醒着你这个城市里尘土的重量
在人字拖的随意下,显得更加晦涩
不会有人停下,一个人的着装
无关街道的走向。破碎的柳荫
杜绝了雨水的另一种可能性
它的出现,似乎更像一头野兽
撕碎一种真实。雨后新草的味道
已经离我们很远,而那个男孩
仍站在空旷的街头,双脚被雨水打湿
多雨的街道
眼镜上的迷雾,玻璃窗上的雨水
车流裹挟着行道树虚伪的绿意
倾泻而下,街角垃圾的酸腐味汇入积水
多雨的街道变得难以言说
它们扰浑城市的灰尘,潜入符号背面的阴影
承载着一个单身白领,一个失恋的厨师
一个没带伞的发廊帮工
和一个时不时偷瞄他的银行协警。
这些我看不见的深处,已变为述说的障碍
在阳光富足的白天,影子尚未被唤醒
而现在,我们通过灯光获取
诱人的寓意,抒情的动力。
昏黄的落日不会笼下美的果园
单调色的转变增添别样的清晰
鱼缸里金鱼同样没有表情,来着的调笑与客套
询问老人的病情只是处于礼貌
我们该怎样在一具身体与消毒衣物旁
从容地谈起衰老与死亡——在一堵雪白的墙壁前
谈资一尘不染。水迹,目光尴尬的藏身之处。
多雨的街道,一切变得难以言说
一切尚早,夜晚未至,白昼从未施加它的影响
月亮的轨迹难以确定,梧桐树不再扮演风景的角色
雨后亮绿的叶子。有时候,我更愿相信
它只是一条水泥铺成的路,难以言说却无关雨水
那又是谁,在我们的谈话中放入沉默的石头
▲《校园风采》本期支持诗社:复旦诗社同济诗社江南诗社(安徽师大)
北京医院哪家治疗白癜风技术好白癜风能治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