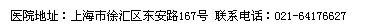您的当前位置:聋症 > 聋症症状 > 来自他方的战争
来自他方的战争
既然都打开了,那么有没有一眼望到头的远方。
家里来了什么客人?我一进院子就听到陌生人的口音。我跑进中屋,看到一个素未谋面的西装男子,勉强操着一口可以让我的爷爷听懂的口音。
他一直在讲,滔滔不绝。我虽然没有听懂他讲的任何一个字,但却一直在目不转睛地听着。这个陌生人,我很喜欢。我第一次,在仅有九年的人生阅历史中,感受到来自他方的声音和味道。他边讲,手上还配有动作,脸上的表情也随之变化。他一口气大概讲了十分钟而没有中断。他的样子,使我我想起了:口若悬河.
我猜测感受到他之所以得到爷爷奶奶盛情对待的原因。
然而我一直在等待,等待一个可以让我听懂的词眼从他的大河里分出支流。然而这样的时刻迟迟不肯到来。那一刻,我真的以为自己要等到地老天荒。
他终于顿了一顿。其间爷爷一直半闭着眼坐在男人对面的沙发里,奶奶在跟爷爷并列的另一席沙发里坐着,堆着笑容,努力去听懂他的话和别扭的口音。而我一直站着,侧耳听。
奶奶同我一样,来自他方。我却比奶奶更快适应这里的语音语调。我毕竟还小,年方九岁。学会和忘记对我来说一样容易——我来的那个地方,早已在九年的离去中化为泡沫。这一点,我没有奶奶幸运。
看到爷爷脸上流露出倦意,西装男子从容地停止了,脸上依旧保持着浅浅的笑意。
爷爷缓缓睁开了眼。
“不然,如果您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的话,可以把电话号码给我一个,方便联系。”
您。电话号码。
我好像一下子惊醒一样欢呼雀跃起来,不假思索地背出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
四六八八二三七九。
这串响亮的数字在我脑海里盘旋,我就像背出语文课文一样高兴。
西装男人把脸朝向我站着的门口,最靠近光明的地方,大方地对我笑了,说:“这姑娘,真是伶俐。”
伶俐。
我不知道它的意思。但是他笑了,一定是夸奖。于是我也笑了。
他低头在纸上写下什么,我不得而知。然后,他把纸和笔都收进黑色的包里,起身要走了。
“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日后联系。”
日后。
我本能地把门口的光明让给这个西装男人。奶奶起身送他到院子口。连他的走路都有他方的样子。我看见他走,下了台阶,经过五月琳琅炫目的石榴树。我看他走,到院子中央,高处一串如雪的槐米正随风飘动。我看见他走,一直走到院子口。消失,从未回头。
马上,奶奶就拖着臃肿的身子折返。
“你怎么那么傻,小伊子,怎么一下子就把电话号码告诉他了?”
我很无辜。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表扬的事吗?
“我厉害吧?电话刚装,我就把号码背下来了。”
“你知道他是干什么的吗?”爷爷问我。他似乎彻底休养过来了。
我愣住了,“我不知道。”
“他是来推销的。要是进去了,至少要千把。”
千把的概念,对于我,就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原来他竟是这么十恶不赦的人。我们这个村子,千把也就相当于半年的收成。
我开始厌恶起这个来自他方的骗局。
“好了,去做晚饭吧。我们也都饿了。”爷爷对奶奶说。
奶奶顺手拿起围裙,揩了揩手,走到院子东边的灶台,开始生火。
爷爷再次闭目养神。我走到石榴树前的月台上,从书包里掏出作业,趴在月台靠墙处的小台阶上细细写了起来,就着残余的光明,趁着黄昏到临之前的夏天。
突然,三爷来了。他走近奶奶,小声给奶奶嘀咕了几句话,我没听清,也根本没有注意。三爷随后走了。留下奶奶满脸惊慌,多烙了许多张饼,够我们全部第二天吃一天了。
“你作业做完了吧?”晚饭时,奶奶问我。
我咽着饼,点头,“全部都做完了,礼拜天都可以玩。”我抬眼,才留意到奶奶写在脸上的惊慌。
“那好,明天不能睡懒觉,六点起来。”有人要来,你必须要躲一躲。
有人要来,我必须要躲一躲。为什么呀?我不明白。
“什么人?”我反问,嘴里还嚼着尚未下咽的饼。
“你不用管。明天起来就好。”向来温和寡断的奶奶一下子变得严厉果决。我不适应,所有的委屈和不解随着饼一起下咽。
第二天清晨,在石榴树上的麻雀开始啁啾之前,奶奶就把我从睡梦中叫了起来。我顶着惺忪的睡眼和无穷的睡意极不情愿地跟在奶奶身后,穿梭在早得没有一只鸟的夏天早晨。穿过那个圆形的场和那片裸露的岩石,奶奶一直把我带到村子最西边的麦田。这时的麦田,葱绿一片,一块连着另一块,风一吹,一层压过另一层,像海浪一样涌动起来,律动而富有生机,同时蕴含着如大海一般辽阔的秘密。奶奶将我置于这无垠的秘密的边缘。在最角落的岩石上,奶奶停了下来,转身交给我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她昨天已经烙好的两张大饼,对我说:“你躲进麦子里,最好是中间。无论如何不要出来,不要乱动,千万不能被人发现。饿了,就把饼吃了。事情过了我会过来。记住,只有看到我来,你才能出来,记住了吗?”
我一直低着头,“记住了。”我不解。我动了动套在拖鞋里的脚趾,发现,朝露把我的裤脚都打湿了。还有奶奶的。我接过她的布包,走到这团巨大的秘密中间。我选好了一片中意的土地,随后扑倒下去,大海里又多了一个小人形的秘密。我透过麦子看到蓝天,看到奶奶充满心酸的一笑,然后走了。我看到我的梦也在对我笑。
现在,整个夏天只剩下我和这个无穷大的秘密了。我枕在柔软而芬芳的布包上睡着了。周边的麦田过滤掉了太阳所有的燥热,洒给我的美梦一片阴凉。我不知睡了多久。我不知什么时候醒来,我饿了。我睁开眼,太阳已经很高了,估计也到了吃饭的时辰。我趴在这块大地上,从包里拿出一张大饼,一边咀嚼一边审视这个属于我的世界。我不能站起来,万一被人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这种大夏天,一般不会有人来这里。除了场子东边的道路上偶尔会出现几个过往的行人,这片岩石和麦田都不会有人来。没人关心这个地方,这里仿佛被全世界遗忘。以前,偶尔还会有几个顽皮的孩子跑来这片岩石上捉蚂蚱或者找美妇蛾。
可不是今天。
我慢慢感受到夏天膨胀的热,从岩石上那棵香椿树上经久不衰的蝉鸣聒噪。这里,唯一向上站着的就是那棵香椿树,只有它符合树的形象,笔直向上,至少也有十米。
我长久地注视着那棵高大的香椿树,试图找到一种安慰。我试着看清楚躲在它叶子中间的夏蝉,我恍惚觉得我们之间有什么共通之处:躲避。不知疲倦。
吃饱睡足之后,我精神焕发,但却无所事事。我不能动,尤其是听到场子东边有人来往时,更加小心翼翼,屏住呼吸。
蓝天之下,困住了一个拥有整个海洋的我。
我仰面卧着,双手垫在头下,我注视着天空,和偶尔从我眼前飞过的鸟儿。在夏蝉的背景之下,我听着风吹过麦子的声音,“刷——沙——”变得连绵悠长,不断向前涌,折射,弯曲,留在深深的耳蜗,回荡久远——那是大海的声音。
我看到的太阳越来越多,一颗颗豆大的汗珠从我皮肤沁出,滚落到我的后背。困意又将我席卷。我压倒几棵新的麦子交叉着垫在我的左耳侧,把布包轻轻盖在头上,遮挡太阳。很快,我又睡着了。
我再次醒来,是因为一阵轰隆,仿佛就在我的正上空。
我惊醒了,却不敢轻举妄动。我缓缓移开挡在我头上的布包,没有在我的视野之内发现什么。我翻过身,循着轰隆声望去——那是一架飞机,不大,大概只能装下四五个人的样子。也很低,似乎就恰好停在了香椿树的枝头。
“轰轰轰——”
我惊恐万分,看着直升机头上快速旋转的十字架不断地画着一个又一个圆。我很担心,害怕它会发现我的躲避,揭穿我,并且把我带去他方,远离把我养大的爷爷奶奶。我害怕极了,紧紧握着新生的野草。我的心跳得很快,我以为我会因此失去心脏。
我攥着布包,紧紧注视着那架飞机。这一辈子,我一定不允许再次陷入这样绝望的害怕。
盘旋了好一会儿,那架飞机还是决定飞走了。它永远地飞走了,我安全了。我心跳渐渐平静,一切又都熟悉起来,我又重新听到蝉的聒噪。好在,我们都安然无恙。
一切的提心掉胆、战战兢兢终究成为过去。
宁静再次恢复。我又耐心地等待,等待从早晨开始的正午,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我尚不会思考,只是等待,时刻都听着岩石上的动静。终于,从场上下来一个越来越清晰的身影,奶奶。她面对着黄昏,越来越近。她笑了,我疯了似的从麦田里跑出来。我自由了!再也不需要躲藏。奶奶在香椿树下停下了脚步,笑魇似一朵傍晚将开的花。我穿过一大半的麦浪和岩石,惊起了深藏其中的许多麻雀。一群麻雀决地而起,一个转弯,飞入了即将到来的夜色,在我们身后的世界消失。
从那以后,我的童年一直是自由而无忧无虑的。直到我又拿了第一名的寒假,我九岁那年的冬天。我兴高采烈地对爷爷奶奶宣布:“看,我又拿了第一名。”奖状在寒风中飘摇似橘树也似黑夜的灯笼。“老师叫我把它贴在墙上。”再过不久,墙上将贴满我的奖状。爷爷奶奶却是一脸忧愁。我转头去看那面墙,空空如也。我惊愕,为什么?
“伊啊,你还是先别贴了。快吃饭,等会去白莲奶奶家。”
白莲奶奶家。我不喜欢。去年去她家走亲戚,我爬上她家后面的荒山。下来的时候,却滚了下来。让我不喜欢的不是自己没站稳,而是摔下来之后他们的嘲笑。
“我不去!”我也可以很坚决地拒绝。
“不行,必须去!”爷爷生气了。我没有再去顶嘴的勇气。在奶奶脸上,我看到了似曾相识的担忧。
我一声不吭,吃完了晚饭,穿上大袄后就被奶奶拎走了。路上,我一边走一边小声哭泣。奶奶却只顾向前,披星戴月,迎着寒风和黑夜。大地上仅有的一束手电筒的光匆匆地在路上行驶。
“奶奶,我为什么要去?”
“就是你要去!计划生育的人又要来了,你得躲一躲。”
计划生育。
“那是什么?”
“唉,你别问啦好没,以后你会明白的。”
我不再哭泣,开始思考计划生育的含义。我突然想到那香椿树上的飞机。大概它们是同一类事物:冰冷,坚硬,令人恐慌。
白莲奶奶家在远离麦田的地方,那估计要远处无数倍。那是另外一个遥远的村子,最靠近县城。躲去那里,应该是安全的。
路途很远,很冷。奶奶领我进去的时候,大概已是晚上十多点的光景。我又一次看到了白莲奶奶和她的一头银色短发,相比去年更白了,她的身子和奶奶一样,都是臃肿的。
她更老了。
奶奶和白莲奶奶坐在炕沿,一边取暖,一边寒暄。昏黄的灯光打在这两位奶奶身上,我听不清她们在交谈什么。奶奶看起来很难过,白莲奶奶也是满眼怜悯。我坐在一旁的凳子上,一言不发,默默地看着灯光那头的两位奶奶,交谈,交换表情,我过滤掉她们的声音,就像看一场默片。在无声的一旁,我独自陷入了去年的悲惨经历。
我已经忘记了究竟是我喊别人跟我一起去爬山,还是我应和了他人的提议。刚开始,那座山还不算难爬,我们几个很快就爬到了那座山的三分之二的高度,它与最后的三分之一之间,留有一块相对宽阔的空地。我迟疑。但是去掉最后的三分之一处,它就相当于一座枯山。所有的树木都长在最高最陡峭的地方。我最后决定继续爬,只是为了不爬一座枯山。而他们都选择待在原地。上去不并是很艰难,很快我就爬到了顶峰。站在山顶,我向下望,仿佛一整座山都郁郁葱葱,一阵风吹来吹过,树叶过滤的风与我擦肩而过,“沙沙沙”很是舒服。山上长满核桃树,仿佛一整座山在秋天都会硕果累累。我很开心。但他们都在原地等我,我只得即刻下山,片刻不得留恋。然而在下山的时候,我一个没有踩稳,摔倒在地,继而整个人像球一样翻滚下去。我顺着山体上来的路向下滚,我以为自己会一直这样滚到山脚,脑子里什么都没有,感受到的只是一片片风和一层层土在我的眼前不断旋转然而我命大,在那三分之二的高度被拦截下来。因为山泥的柔软,我并没有受伤,只是头有些晕,而且全身沾满了泥,全耳都是他们的嘲笑。我站起身来,拍干净了身上的泥,走下他们的枯山。
我下意识地摸了摸头,仿佛上次的头晕持续至今。一阵风从窗户的缝隙吹起来,我冷得打了一个寒颤。
“好冷啊。”我低语。
“睡吧,闺女都喊冷了。”白莲奶奶向来安详温善。
“伊啊,过来,把鞋子衣服脱了,上炕上来睡一觉吧,明天下午我们就可以回去了。”
我又想到计划生育这个让人毛骨悚然的词。我怀着胆战心惊的惶恐脱掉了大袄,脱掉鞋子,脱掉棉裤,然后一头钻进炕上的被窝里。我睡在最边上,白莲奶奶睡在中间,奶奶睡在另一个边上。白莲奶奶刚把她臃肿的身子拥入棉被,我就闻到一股老太婆的味道,但是屈服于我的害怕,我没有任何抱怨。
然而我总是瑟瑟发抖,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害怕。我一直向下钻,一直向下钻,很久都没有睡着。我听到奶奶已经开始打鼾了,十分熟悉的声音,我觉得有些放松。不知过了多久,我又听到从脚底下传来几声鸡叫:那是隔壁的鸡。或许是冷了,或许是闻到了来自他方的味道。
我仍然在抖,像一只新生的小猫或者小狗,总是抖个不停,无休无止。我的脚突然踢到一块砖,冰冷坚硬,瞬间我想到了那架停在香椿树上的飞机,也是这样的,还有那个西装男人。我抖得更加厉害。
“闺女,你怎么啦?”原来白莲奶奶也还没睡着。
“我害怕,”我的声音都是颤抖的,“我以为是战争。”
“夜还是一样的黑,可是闺女,你已经在别的地方了。没关系。”
没关系。
不管是骗局、嘲笑,或是战争,都远在他方。
黎子白杨说
点状白癜风会自逾吗哪家治疗白癜风最出名